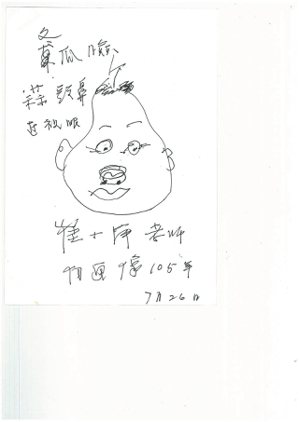【文學紀念冊】露冷春風絳帳寒──敬悼戲劇家崔小萍老師 ☉ 亮軒
這一處墳場離家很遠,就在一大片微微起伏的田野裡,有幾處墳墓錯落散布其間。墳前有石板的小桌。我懷裡揣著幾張空白稿紙,我要到這裡來寫幾段戲劇的台詞。對一個初中生,倒也不覺困難,若已經上大學,大概沒有這樣的膽量。
稻禾高到了膝蓋,順著窄窄的田路、踢踢蹭蹭一路走了過來,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寫戲詞兒,就到了這兒,一個我逃學的時候常常路過或是停留的地方。頭上清清爽爽的藍天白雲,腳下密密雜雜的青草,放眼四圍,最近的人家也在遠遠的山邊。
就在石板上寫下若干喜怒哀樂兼老少的段子,有哭有笑有憤怒。別無選擇,我非寫不可,因為中廣的崔小萍導演說,你去找找劇本,選幾段,星期六下午兩點來試音。「劇本?」十二歲的男孩沒見過。若回說沒見過,就怕她把我給否決了,想當廣播劇團團員的夢想就成了泡影,我點頭如搗蒜,這就是在這兒炮製段子的來由。
六十多年前,廣播是最廣泛傳播媒體。而最大的電台便是中廣,在全台灣有二十三個分台。當時收音機都是大型的傳播工具,有時一個村子也只有一座,整個部隊也常把大喇叭掛在大樹上,定時播出中廣的新聞與節目。廣播節目中最受歡迎的,就是每個星期天晚間全國聯播節目的廣播劇。在廣播劇播出時段,街上行人稀少,家家都在聽。五十分鐘的劇播完了之後,「以上廣播劇是由崔小萍導演,李林配音,唐翔錄音……」人人耳熟能詳。家家店面,只要有收音機,都把喇叭朝街上聲音放得大大的,便是一路上從頭走到尾,幾乎可以聽完整齣的廣播劇。
崔小萍的大名無人不知,她有時也參與編劇、演出。我小學時聽到她演《清宮祕史》,那個慈禧太后的威嚴、狠毒,似乎這個老佛爺的幽靈就活在真空管裡。當時大家都窮,看電影的機會很少,聽廣播劇不用錢,卻是每周一次不可省卻的享受。早年北平曾經有一位說書先生在電台說書,他的節目播出時,街上一定行人稀少,此人姓王,因此有了「王靜街」的名號。崔小萍導演也許同樣可以尊之為「崔靜街」。從孩提到少年,許多廣播劇演員的名姓,還有他們主持的節目,個個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大明星,我也想當大明星。幾天以前,我終於決定自薦報名。建中對面史博館前有個公用電話,就直接打了去,請「崔女士」說話。那時還搞不清該怎麼稱呼。
電話那頭真的就是崔小萍,我嚇得頭髮根根豎立。我終於自道了身分,不料她很和氣,因此我的膽子也就大起來,迫不及待的要跟她見面,跟她說我要參加劇團,可不可以現在就去看她?她遲疑了一下,問道你下課了嗎?
我從建中走到了當時在新公園邊上的中廣,著童軍短褲制服,背著書包,見到了此生結緣甚深的崔老師。
她個子小,腳下高高的高跟鞋,腦後緊緊的紮了一根辮子。連身裙裝到腿肚,顯得很俐落。高跟鞋在地板上篤篤篤篤的,小個子的人步履都急。胸前掛著一只碼錶,後來發現,她是我一生見過使用碼錶最神乎其技的人,排演廣播劇,不論中間多少次重來喊卡,只那麼一趟,錄製完成的廣播劇錄音帶計時,跟她碼錶上一秒不差,從來用不著重新再算。
平生第一次進發音室,四壁都裝著柔軟的隔音皮墊,聽得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我照著我寫的那幾段詞兒,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立在麥克風前,也不知她去哪兒了。突然之間她的聲音響遍發音室:「開始!」我吞了口唾沫,照著自己寫的段子演了起來,她坐在對面控制室角落,根本看不到。老師導廣播劇,只管聽,從來不會從大玻璃窗看看我們。老師聽到哪一段有問題,就從擴音器中傳話:「卡!再試試。」要是一試再試都沒達到她想要的標準,她就示範一次,那時我們當中任何人,個個突然覺悟真就該那麼演!比老師年紀大的演員常見,有的十分知名,她一視同仁,感覺上沒有一個不怕她,不是因為她有多兇,而是因為那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碼錶永遠在胸前的崔老師,說話簡潔有力,是我心中永遠的形象。
演完出來,老師走過來說了一句:「聽起來你很有經驗嘛。」真的不知她講的是真是假,總之,她錄取我了。我激動得沒法說話,深深一鞠躬就忙忙下樓。老師從上面梯口叫住我:「小弟弟,我們廣播劇演出沒有什麼酬勞,只有一點車錢。」我連連點頭而去,誰要錢啊?
一個星期後,我接到了老師寄來鋼版油印的劇本,我的角色是個在少年觀護所的小流氓頭,一共有八句詞兒。這八句詞兒,就是我進入廣播生涯、戲劇世界,再到文學美學哲學世界的開始。
幾個月之後,我就想該當個劇作家了。我讀了幾齣啟明版的外國劇本,想要更上一層樓。有點怕直接跟她說,寫了一封信去。後來老師當面告訴我,要是對戲劇有興趣,就要讀藝專影劇科,好好的學。這幾句話暗藏心中,我不可能跟家裡的長輩開口,除了換頓打,什麼好處都沒有。專科學校聯考前,我背著大人,偷偷改了志願,第一志願便是藝專影劇科,這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大多數人都把它填作最後一個志願。我終於當了崔老師的學生,而且,加入唯一需要通過測試的編劇組。
老師的專職在中廣,藝專為老師預備了一個走廊邊小小的單間,門前有幾棵小樹。老師在有課的前一天便到小單間來住宿,有時也利用這樣的一個晚上趕劇本。我常常就在門前的走廊上跟老師說話,師生二人在燈下站著可以說到夜闌人靜。我的問題很多,老師也都把她的經驗心得一一告訴我。那個時候方知老師真的是厚積而薄發,她讀過的戲劇方面的書真多,也知道了她不見得都是從第一場開始寫,常常是從中間的某場發展擴張而成全劇,我覺得匪夷所思。
之後老師更是頻頻找我演戲,她導的《窗外》就以我們青田街的家為主要的實景,我則擔任場記。服兵役之後,我主動考入中廣,成為正式的廣播員。
崔老師在電台的風格跟許多人不一樣,她從不閒扯,更不搭腔,有交情也是工作關係。跟上級簡直不來往,打牌吃酒她都不會。她孤獨,然而充實,並不寂寞。但是後來她受到了一次打擊,是在她所受更大的所謂匪諜案的打擊之前。
中廣應該還是保存了老師導演的廣播劇一千部左右,她劇本寫得也非常好,後來知道老師早在二十幾歲大陸時期就導演了許多齣中外名劇,共同合作的許多人都是近代兩岸戲劇史上響噹噹的人物。廣播劇之於她,應該算是小試牛刀了,人人折服。可是,忽然之間有一天,導播組長宣布,以後廣播劇導演由每個導播輪流擔任。我沒有聽到崔老師任何一句抱怨的話,然而她一定非常失落。這是外行領導內行最典型的例子,把藝術家的工作當作會計一般。我不認為這跟她後來涉嫌匪諜有什麼關係。只見老師用更多的精神放在戲劇教育上面,成了她一生的志業。
過了一段時間,發現她忽然好幾天直到好幾個星期都沒來上班,漸漸傳出她被捕的消息。
在那個年頭,要抓誰就抓誰,一年半載才知道人在何處的很平常,有無生死不明?不得而知。就這樣,崔老師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快十年。這十年間,我曾兩度進出中廣,也成了家有了孩子。
有一天,公司有人私下問我說明天要請剛出獄的崔老師吃飯,你來不來?
是個大寒流的冬天,我們一致很驚訝的是看來老師依然年輕,歲月沒有在她多難的生命中劃下太深的刻痕。她依然話少,也沒有太傷感的樣子。餐後,我私下邀請老師到家裡坐坐。
老師在我的書房跟我們夫妻兩人徐徐道出了她受到的十年折磨的故事,她講得平靜,不覺到了天亮。我們聽得毛骨悚然。從她的陳述中,有兩點我永遠忘不了,一個是那些人從來不用證明你是不是匪諜,他們用各種方式折磨你,要你恨不得千方百計變成真正的共產黨,槍斃了算。但是他們不一定接受,於是繼續受折磨,直到他們同意你終於是個共產黨為止。老師說,他們接受了她無休無止的供述,終於停止偵訊之後,回到牢房後她大哭了一場,那一種受盡欺凌的況味,是江河一般的淚水也洗不盡的。
另外,老師說了一句話,差不多是結論,她說:「要是你,一定早就自殺了!」「為什麼?」「因為你聰明,越是聰明的人越是受不了。我傻,才活了下來。」
這一句話,到如今我還在想。
老師是傻,人家約談她一次又一次,她嫌煩,居然自己收拾個小包包跟人家說,我就住在這兒,講清楚了再走。另外她又主動把一生的日記交了出去。她的確是坦蕩蕩,人家一點也沒領情。老師是個天大的呆子。
第二天,我們昨天跟老師吃飯的事讓人給報告了上去,受了警告。
那些人應該明明知道她絕對不會是個匪諜,卻必欲置之死地,非常可怕。判決書上也只說她曾經「意圖」顛覆政府,卻沒有證據。然後又說她在台演出許多左派的戲劇,但那些戲劇都是政府核准演出的。老師卻被判了無期徒刑。直到老總統去世,才獲得減刑,足足坐了九年四個月的牢獄。
老師仁厚單純的本性未變,記得老師在她的《天鵝悲歌》新書發表會時說,她從前就是基督徒,但是在受難時才發現先前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受難後才是。我想老師以性命證實了善良是無限的,信仰也是無限的,老師是人性光明面最崇高的典型。
今年2月1日,大年初五,老師還跟我們在一起歡聚,聽她唱她最愛唱的〈初戀女〉。老師一向就那麼純真。記得幾十年前,吉永小百合出道未久,演出了一部純情愛情片,老師看了,感動到不行,就掏錢請一夥又一夥的人去看這部電影,她也一次又一次的帶著面紙去陪哭還是獨哭。這麼善良純真的人,任誰一眼就看得出她不會是個匪諜,要是共產黨會派她來顛覆我們的政府,共產黨不會有今天。
但與老師相處,六十多年來我們語不及私。至情無語,許多話都深深的藏在心裡。
今年2月18日,電影中心為老師辦了幾天的一生回顧展,好多朋友學生圍在她身邊,她非常高興,第一天就一連看了兩場,一場是她導的,一場是她得到亞洲影展最佳女配角的作品《懸崖》,李行導演也在場陪著她。誰會想到幾天後,她就住了院,看看沒什麼,都要出院了,最後兩天卻一落千丈。
我趕到老師的床前時,老師剛剛離開人世,身邊有幾個常陪她的學生。牧師說,人的耳朵是最後失靈的。我俯身輕輕撫弄著老師的滿頭白髮,端詳著老師沉靜的容顏,我附耳跟老師說了些話,都是在她活著的時候不會表達的言語。我謝謝老師引導了一個不懂事的莽撞少年,走上了他一生無悔的路。如果不是還有別人在床邊,我一定會深深的吻她,淚水一定會滴在她身上,那是犯忌的。恍忽間,覺得六十幾年來從來沒有像此刻一樣跟老師那麼親近,那麼相知。我到底沒有說出老師我愛你。現在,老師,我要跟您說:「老師,我愛你!」
【2017/03/31 10:41:34 聯合報】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8/2375390